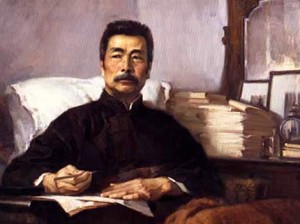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网址: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6/23/the-sound-of-one-hand-grasping/
这个月(6月)初在美国对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纪念活动出奇地不声不响,尤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群体中更是如此。89年事件发生后的几年,情况可是大不相同。我当时正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啦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学生,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那时在美国大约有40000名中国学生。北京进行军事镇压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予这些学生政治庇护和永久居留权。
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天安门前的抗议活动很少有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当时作为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在欧美国家形象颇为高大。我们所遇到的学生都以近乎传教士式的热情,表达了他们对民主的拥护(或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而且是带着毋庸置疑的真诚。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在图伯特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时常是相当恼人,甚至是令人憎恶。
在位于伊萨卡(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举行的一次会谈中,仁青达洛啦(Rinchen Dharlo la)在我和拉藏啦之前发表讲话,他当时刚刚被任命为达赖喇嘛驻纽约的代表。听众席上的中国学生用非常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他说话,并且指责他提起图伯特议题。他们声称中国民主才是最为优先的问题。一旦他们推翻了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才能讨论图伯特自由问题。我指出,有同样的可能性出现相反的情况,新政权有可能对图伯特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和更加残酷无情。有个人高声打断我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笑着回敬道:“中国人民何曾对自己的政治有过丝毫的发言权?”拉藏啦也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反唇相讥。
在随后几个月我们遇到一些天安门广场上实际活动人士,诸如柴玲、沈彤、吾尔开西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图伯特问题上的态度都自相矛盾。但是流亡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和中国异见人士“开展工作”的好时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甚至动用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基金来“培养”这些人,而最终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ICT的工作人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关照这些中国异见人士,并将他们介绍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但是在这些异见人士当中,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表达他或者她对图伯特事业的支持。他们发表的少数几份措辞谨小慎微的有关图伯特人权的声明,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们即便不这么做,也没人会真的当回事。那么这些所谓的异见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现在都身居何处呢?根据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在2003年所著的《坏分子:从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者》一书,这些人或是变成了野心勃勃的商人,或是华而不实的媒体顾问,甚至是纠缠于经常是你死我活的“窝里斗”。
这并非是说在图伯特问题上没有真正的汉人朋友。最早和最坚定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之一魏京生,就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图伯特事业。记者曹长青曾写过两本小册子,讨论有关图伯特争取独立的权力,以及为了图伯特人民的生存而争取独立的必要性。资深劳改问题研究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今年三月在达兰萨拉公开发表讲话,坚决地支持图伯特独立。但是 由于某种新闻审查行为,CTA的网站没有报道他的讲话,演讲的视频也没有公开。我个人结识了很多中国活动人士,尤其在2008年。最近以来,一个笔名为更桑东智的汉人异见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独立翻译我的每一篇文章(据知,翻译得相当出色)并在汉语网络世界进行传播。而我并没有付给他一分钱,也没有把他介绍给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请浏览他的网站。
但是最近以来,流亡当局并不待见那些号召图伯特独立和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汉人朋友。他们想要的汉人朋友是那些愿意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制定的对中政策的人,即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尊者自己对 “中间道路”的成功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2010年,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时,尊者宣称“最终我将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为了让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若干年以来,流亡当局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工作拓展计划”。
在2010年7月,尊者在他的推特上向中国民众发布消息,并接受他们的提问。但其实在这段“推特”插曲之前,尊者就曾经利用采访和与国际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向那些现在通常所称的“汉人兄弟姐妹们”伸出橄榄枝。
在2008年《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尊者试图将1959年的以前的汉藏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热烈而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以前通常所以为的“痛苦而敌对”:
如你所知,直到1959年,博巴对汉人的态度都是亲密的,非常亲近,这是很正常的。在拉萨,人们提到汉人商人的时候都带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当然在图伯特,人们听到共产党的名字都会害怕,因为人们了解在蒙古以及苏联的部分佛教社区所发生的事情。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军队进来,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粗暴蛮横。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只是抱怨这些“坏共党”,但是我们从来没说“坏汉人”。从来没有。
尊者的努力不仅仅是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还尽一切努力在各种行程中,亲自接见汉人群众,甚至包括前往达兰萨拉的汉人旅行者和观光客。这些人当中包括了尊者在公开讲话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支持他的“中间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李江琳、丁一夫和陈破空。他们都声称“在很多不同场合见过达赖喇嘛”。这些人给人留下的表面印象是同情图伯特的,而实际上他们也在写作有关图伯特的东西并号称是图伯特问题专家,但是在更为核心的政治问题上总是无一例外地模棱两可。他们似乎都不在北京的黑名单上,甚至都没有过“进局子”的记录。一个在CTA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最近以来,尊者接见的中国访客要多于任何其他外部团体。这一点让很多博巴感到困惑,尤其一些退休的官员,其中有一位曾经跟我谈过此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这些形形色色很轻易被引见到尊者面前(这是一项连很多博巴都无法享有的特权)的中国访客中,肯定有一些是来自中国情报部门的密探。
我确信读者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上读到过有关中国庞大的间谍计划,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大学、研究机构,或许甚至包括军队和政府机关进行渗透,从而获取机密和影响美国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利用访问学者、大学生、游客和其他貌似无关紧要的访客。达赖喇嘛接见的那些人也大致如此。在达兰萨拉有很多已经充分证实的安保漏洞。有一次,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安保漏洞并问责有关官员。当时的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教授淡定地声称,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博巴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中国人的海外谍报行动主要受中国国家安全部(MSS)的指导。但是在有关图伯特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共统战部,这个机构负责处理与达赖喇嘛的谈判。达兰萨拉还乐颠颠地对这个机构的职能懵懂无所知,而根据2010年加拿大出版的一份材料显示,这个机构的职能包括在旅居海外的华人(和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中招募密探、控制中国留学生、对外宣传以及长期潜伏行动。
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达兰萨拉的绝大多数博巴都令人忧心显得地不谙世事和天真幼稚。达拉萨拉对间谍的妄想症总是针对那些来自图伯特的“新人”。总体而言,这些“新人”当中的间谍数量寥寥无几,不过在去年的一起案件中,印度警方抓获了一个名叫边巴次仁的人,他被指控为间谍,计划实施“恐怖主义投毒阴谋”。结果证明他只不过是中国公安部门的一个小角色,而他的所谓“恐怖主义阴谋”也一事无成,因为CTA安全部在初步报告之后并无其他跟进报道。
但是,很多貌似腰缠万贯的中国游客和朝圣者,当然还有那些达赖喇嘛对其敞开大门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的“知识分子”们——这些人似乎完全免于安全检查。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很多流亡宗教组织把这些人看做是有利可图的施主或供养人(jindaks)。
尊者似乎确信通过开展这种与中国访客的面对面交谈,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国对他自己的看法,并且无疑正在赢得中国的信任和同情。不幸的是,这些人当中至今也没有几个人公开站出来表示他们对“中间道路”计划的支持。
有些人说,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曾经发表过一些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言论。但是通观他的讲话,人们也只能看到一些认可图伯特“自治”和支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表述。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支持“中间道路”政策。唯一真正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王力雄。但是,在一篇有关今年一月被捕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的文章中,王力雄写道:
“他(伊力哈木•吐赫提)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此类“工作拓展”的努力并非仅限于尊者接见中国访客,甚至在CTA内部已经体制化,能说汉语的“干部”们被分配到纽约、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拓展”岗位上。同形形色色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汉人,举行座谈、派对和社交集会。这些项目得到了尊者的鼎力支持,并且可以享有其他部门无法获得的资助。
迄今为止,尤为重要的一项“拓展”活动是在2009年8月6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名为“寻找共同点”的一次中藏会议。据会议组织者介绍,与会者包括“超过100名中、藏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和人权倡导人士。”参加会议的二十余名中方人员的开销全部由CTA承担,其中包括严家其,他当时居住在美国,曾经是被赶下台的前中国总理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在2005年去世。尊者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
| 尊者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讲话 |
在这次会议的“最终文件”上并没有对“中间道路”政策的认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其表示“尊重”的妥协性表述。会议通过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其他五项核心决议包括这样一些善意而无关痛痒的建议和言论,诸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民主化密切相关”。决议还号召中国民众认真反思“汉族沙文主义”(这是毛泽东1956年描述汉人优越感的时候创造的术语),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遵守法治原则。”决议的最后也是最软弱无力的一条指出,达赖喇嘛返回他的祖国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最后一条决议引发了有关达赖喇嘛访问五台山的一些讨论,以此作为尊者“返回祖国”的第一步。“他去五台山朝圣的愿望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一位与会者指出,“当局担心达赖喇嘛的任何一次访问都会让那些强大的潜在势力脱离掌控”,因此,即便是“纯粹去五台山朝圣”也不会得到许可。
我想,这次会议一定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共同认知中结束的:现实难遂人意,中国拒绝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更不用说流亡当局。
流亡当局,包括司政洛桑森格本人,已经把达赖喇嘛的“拓展对中国的工作”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战略政策。在2008年发表于故乡网(Phayul)的一篇文章中,司政详细阐述了为何这样一个战略对于解决图伯特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举圣雄甘地作为例证,司政说甘地同“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培养友谊,从而获得他们对他的事业的支持。显然,司政先生在此处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甘地从英国、非洲和印度的白人民众那里赢得的几乎所有友谊,都是基于各种共同利益、活动或信念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以赢得政治支持为前提的“培养”。
其次,那些支持甘地的英国人或其他人,尤其是司政提到的Madeleine Slade和Rev. C.F. Andrews,他们都坚定地支持印度从英国赢得独立的自由斗争。甘地无需在争取独立的目标上同他们进行妥协,无需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稀释我们最初的目标:从独立到“中间道路”,然后到司政的“部分中间道路”(放弃民主制度,甚至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最后只剩下对“中间道路”“表示尊重”,就如同日内瓦会议决议的表述。
还有另外一些印度独立事业的英国支持者,比如著名的Horace Alexander和Wilfred Wellocks,他们成立了印度自由委员会(Council for Indian Freedom),把桂格党人、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劳工党人团结在一起声援印度独立事业。我发现甘地的英国支持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兰开夏郡(Lancashire)格林菲尔德纺织厂(Greenfield
Mill)的纺织工人,他们因为甘地抵制英国货的斯瓦代希运动(Swadeshi)而丢掉了工作。在下面这张甘地于1931年访问这家纺织厂的著名照片中,甘地不仅没有碰到预想中的麻烦,反而受到了那些失业工人热情洋溢的欢迎。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拓展工作”,也不应该是针对那些自私自利、自吹自擂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是应该面向真正的中国民众,那些在中共的统治下挣扎的民众,那些渴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达赖喇嘛应该成为那些我们在中国的真正“兄弟姐妹们”的代言人——那些被剥夺和被压迫的人:那些“癌症村”里数以万计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那些在劳改营里遭受奴役的人;那些因旨在造富中共达官贵人的开发项目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他还应该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练习者仗义执言:这些人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正在遭受中共政府残酷无情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