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kra Thubten Choedhar (1925-2012), In Memorium.
作者: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
翻譯:更桑東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发表于:2013年6月26日
题图说明:然扎仁波切在繪製唐卡。攝影: Mesum Verma
“首屆圖伯特全國作家會議”于1995年3月15日至17日在達蘭薩拉召開。來自印度、尼泊爾、瑞士、英國和美國的65名作家和其他代表,參加了由阿尼瑪卿研究會(Amnye Mach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這是圖伯特社會有史以來首次舉辦這樣的會議。毫不誇張地說,對於圖伯特文學界而言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甚至有圖伯特境內的作家,從遙遠的安多西寧通過電話與我們取得聯繫,表達他們的祝願。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給我們發來了賀信,同樣發來賀信的還有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偉大的波蘭異見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他在信中說:
“請接受我的祝願,我與你們休戚與共、感同身受。我也曾長期流亡,我理解你們面臨的問題和擁有的希望。你們在世界上很多國家贏得了自己的朋友,你們應該堅信,你們在孤絕的境地中進行的寫作,有朝一日必將為世人所知,並被世人心懷感激地銘記。”
參加這次會議的最年長者是然紮仁波切(Rakra Rinpoche),他或許也是最著名的圖伯特作家,當時71歲。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博巴都對他有所瞭解,因為他曾經為偉大的圖伯特學者和詩人根敦群培(Gedun Chophel)撰寫了傳記。然紮仁波切所著的不僅僅是第一部詳細成書的根敦群培傳記,尤為重要的是然紮仁波切還是根敦群培在拉薩期間的學生,師從根敦群培學習詩歌藝術(念阿,nyenga)和文學(宗日居则,tsom rig gyutsel)。
 |
| 然紮仁波切和根敦群培啦在拉薩,約攝於1949年。 |
在圖伯特流亡社會,眾所周知,然紮仁波切是圖伯特古典詩歌藝術(博語為念阿nyenga,梵語為kavya)最為技藝嫺熟的創作者之一。儘管受制於形式規範,仁波切的作品依然能夠帶有一些“離經叛道”,有時甚至是幽默的色彩。他創作過一篇勸世詩歌(Khe-drong-yak sum gyi lo gyue)。在這首詩歌中,一頭同樣鼎鼎大名的犛牛對偉大的學者根敦群培抱怨圖伯特民眾的寡情薄意。這頭犛牛列舉了亙古以來為博巴們作出的無可估量的奉獻,而忘恩負義的博巴卻不知投桃報李,不僅沒有將犛牛的威嚴形象描繪在國旗上,反而用了一種神話中的動物,讓人們想起獅子狗。
然紮仁波切在流亡社會可以說是一位無冕的桂冠詩人。在歷史學家夏格巴·旺秋德丹(Wangchuk Deden Shakabpa)的不朽著作《圖伯特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出版時,然紮仁波切為作者創作了幾首韻律詩。這部著作再版時,稱心快意的作者將這些詩歌全文收錄於書中。在此摘錄其中一段:
美妙的千弦之琴,向世人傳達真相,
千百個變動的音符,真實無妄,
你當仁不讓,
將我們歷史純潔的歌謠吟唱,
喚醒芸芸眾生,遠離無盡夢鄉。
1969年,在圖伯特全民起義十周年之際,知識出版社(Sheja Publication)以小冊子的形式散發了仁波切創作的長詩《來自庫達鳥的消息》(The Message of the Khugda Bird)。在圖伯特關於鳥類的神話傳說中,這種鳥被認為是百鳥之王布穀鳥(庫玉khyu-yug)的傳令官或信使。
 |
| 版畫《難民》(Flüchtlingen) 作者:哲彤·然紮 |
在仁波切的詩歌中,這只信使鳥從圖伯特一路飛往印度。途中,它遇到一位流亡異鄉的年輕人,它向這位年輕人描述了圖伯特民眾在中國的軍事佔領之下,遭受的可怕苦難。
我想是在同一年,仁波切製作了一幅出色的木刻版畫,內容是一位元母親帶著孩子逃離遭受戰火蹂躪的圖伯特。這幅名為“難民”( Flüchtlingen,德文)的版畫,被複製為很多印刷品和明信片,用來為裴斯塔洛齊兒童村(Pestalozzi Children’s Village)募集資金。
在行進的道路上,
所有半途而廢的念頭早已拋在腦後,
我們的雙腳催促我們邁步走向圖伯特,
走向拉薩,眾神的住所,民眾的聚集地,
這裡是所有博巴的首都,她比生命更加寶貴
朋友啊,請不要現在就敬上迎賓的美酒,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歡聚、暢飲和慶祝,
讓我們首先去往覺康(大昭寺),
把覺臥仁波切敬拜。
然紮仁波切還會為像洛薩(圖伯特新年)這樣的圖伯特曆法中吉祥的日子,創作了一些應時應景的詩歌。他通常用自己原創的韻律詩給達賴喇嘛和尊者的兩位老師——林仁波切(Ling Rimpoche)和赤江仁波切(Trijang Rimpoche)獻上新年祝願。一位圖伯特文學家告訴我,如果尊者的私人秘書費心保存這些詩歌,應該可以編輯成冊了。
這位多少有些不合規範的圖伯特喇嘛出生于1925年(博曆火牛年),父親是哲彤·久美嘉措(Gyurme Gyatso Tethong),後來曾擔任德格總管(Derge chikyap),母親是卓瑪茨仁(Dolma Tsering),娘家姓氏為絨迪吉林(Rong Dikyiling,全名為迪吉林夏旺茨仁繞丹Dikyiling Sawang Tsering Rabten)。來自德格大寺的堪欽阿旺桑丹洛卓(Khenchen Ngawang Samten Lodroe,1868-1931)給這個男孩取名為仁增朗傑(Rigzin Namgyal)。在兩歲的時候,他被認定為康區帕雪(Pakshoe)寺的第六世然紮仁波切。這位男孩的父親一開始不同意他出家為僧,但是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親自認定之後,久美嘉措只好放棄自己的兒子。達賴喇嘛給這個男孩取名為然紮•土登曲紮(Rakra Thubten Choedar)。
 |
| 然紮朱古(左側馬上)被帶往八宿(Pakshoe)寺。右邊馬上是他的哥哥索朗妥覺(Sonam Tomjor)。攝影:哲彤•久美嘉措(Gyurme Gyatso Tethong) |
然紮仁波切首先在八宿寺接受教育,並從1935年開始在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接受正規教育,主要是在果芒紮倉的崗如康村(Ghungru khamtsen)。他天資聰穎,有很好的學習能力。非常幸運的是,他的首席經師是一位學識淵博同時具備非同一般的寬廣胸懷的格西(geshe,相當於佛學博士)。這位格西似乎給年輕的然紮仁波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後來的生活中,他時常提到他的老師,甚至在和像我這樣的人的交談中也不例外:
“我的老師,格西•阿旺巴登(Geshe Ngawang Palden),像父親一樣對待我。他是一個心胸開闊的人,他喜歡(民間)舞蹈,喜歡唱歌。他給我講述了很多動聽的故事。他也非常虔誠。”
通常,完成涵蓋佛學各個方面知識的完整格西課程無論如何要花費12年甚至到40年的時間,這還不包括密宗(tantric)部份的修習。而然紮仁波切只用了10年時間,在19歲時獲得了格西學位中最高等級的拉然巴(Lharampa)稱號。
他隨後進入拉薩的居麥寺(Gyume,即“下密院”)開始佛教密宗的修習。與在哲蚌寺一樣,他的修習成績非常出眾。在居麥寺的生活是艱苦的。那是整個圖伯特地區對所有學僧實施佛教戒律(vinaya)最為嚴格和苛刻的少數寺院機構之一。這個寺院還與眾不同地並且毫不妥協地實行平等主義,在寺院紀律和生活條件方面對待高級喇嘛、貴族兒子或者來自農民家庭的僧人都一視同仁。然紮仁波切後來這樣回憶他在居麥寺的生活:
“我在居麥寺度過了一生中最為愉快和歡樂的時光。我們平等相待,刻苦學習,吃著同樣的食物,睡在同一個大廳裡,一起長途跋涉。那是一段有很多清規戒律的艱苦生活。”
在此期間,然紮仁波切開始師從偉大的學者根敦群培,學習圖伯特古典詩歌藝術(nyenga)和文學(tsom rig gyutsel)以及高級文法(sumtag),並且開始對根敦群培有所瞭解。當時,根敦群培啦住在果芒康薩(Gomang Khangsar)的一所小房子裡,位於帕廓地區的北端,離居麥寺很近。然紮仁波切的哥哥索朗妥覺(Sonam Tomjor)當時是哲彤家族的領袖。他是根敦群培的密友和酒伴。
1949年,在他23歲時,然紮仁波切在下密院獲得了俄然巴學位。在下密院的最後一年,作為獎勵,他還被授予“鐵棒喇嘛”( gyegoe)的頭銜。
 |
| 然紮仁波切(居中者)作為鐵棒喇嘛,帶領居麥寺的喇嘛們行進在拉薩的默朗欽莫法會(傳召大法會)上。攝於1950年2月到3月間。 |
在格魯派的學術等級中,同時擁有拉然巴和俄然巴(Ngagrampa)學位的喇嘛並不多見。顯然,然紮仁波切必將在官方寺院系統中大有作為,甚至最終成為甘丹赤巴(Ganden Tripa,甘丹寺法台)也並非不可能,這是格魯派等級中最高的佛學和學術職位。
然而,他在第二年還戒於他的根本上師莫確仁波切(Mogchok Rimpoche)。當時,他的哥哥索朗妥覺被任命為設於噶倫堡的圖伯特貿易代表處助理,已經離開拉薩去了印度。1950年9月,在共產黨進攻昌都前大約一個月,他的姐姐拉旺·洛桑德吉(Lobsang Deki Lhawang,我的母親)帶著然紮仁波切和我一道,離開拉薩前往印度。我(嘉央諾布)當時年僅一歲半,唯有一張泛黃的照片確切地證實當時我也在場。這張照片拍攝於拉薩老城旁邊的八朗學(Banakshol)屋頂上,照片上有我的母親和然紮仁波切,以及還是個嬰兒的我。
 |
| 然紮仁波切,我(JN)和我的母親在八朗學哲彤家宅院的屋頂上。攝影:哲彤•拉旺普格(T. Lhawang Pulger) |
在噶倫堡,然紮仁波切開始跟隨俄羅斯東方學家喬治•羅列赫(George Roerich)學習梵文,之前根敦群培曾給他寫過一封推薦信。仁波切後來在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創辦的著名的聖蒂尼克坦國際大學(Shantiniketan)繼續學習梵文,並且在那裡開始接觸印度和西方的繪畫與藝術。國際大學希望他留下教授圖伯特語言和佛教,但仁波切當時獲得了印度政府的獎學金前往位於浦那(Poona)的班達迦東方研究院(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跟隨Vasudev Gokhale教授繼續他的梵文研究。
 |
| 然紮仁波切擔任全印廣播公司(AIR)新聞播音員。大約攝於1959年。. |
1956年,然紮仁波切進入全印廣播公司(All India Radio)博語部,並在那裡工作到1960年。他同時還在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擔任梵文助理講師。1959年他同來自拉達克(Ladakh)帕耶(Phey)的拉傑•桑丹卓瑪(Samten Dolma Lharjé)結婚。卓瑪啦當時在全印廣播公司的拉達克語部工作,她的家庭是拉達克傳統醫學(lharjé)世家,她的父親是當地非常有名的醫生。
1960年,然紮仁波切應達賴喇嘛的哥哥塔澤仁波切之請,前往瑞士管理安置在裴斯塔洛齊國際兒童村(Pestalozzi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Village)的圖伯特流亡兒童,這個兒童村最初是在二戰後為接納歐洲流散兒童而創立的。然紮仁波切原來打算繼續進行他的圖伯特和印度佛教文學研究,並希望去英國從事研究工作。但是,他明白當前任務的緊迫性,於是接受了請求。
 |
| 然紮仁波切、卓瑪啦和他們的女兒茨仁曲珍(Tsering Chounzom)抵達裴斯塔洛齊國際兒童村。 |
1960年10月,然紮仁波切和他的妻子卓瑪啦,以及20名圖伯特流亡兒童開始了在裴斯塔洛齊兒童村的生活。兒童村中的“博巴之家”( Tibeter Heim)名為“雍布拉康”( Yumbu Lakang),是一座三層的瑞士農舍,其中沒有佛堂。所以然紮仁波切著手進行改造,他設計了一個傳統的佛壇,並親手用粘土塑造了一尊佛像放置在餐廳佛堂的中心位置,以使孩子們在進餐前就可以念誦佛教祝禱詞。達賴喇嘛的一張大幅油畫肖像也放置在那裡。
然紮仁波切還為孩子們編寫了自己的博文教科書。我記得其中有一本是《佛陀的童年》(Children’s Life of the Buddha),他親自編寫並繪製插圖。而後在裴斯塔洛齊的辦公室裡逐頁複印並裝訂成冊。然紮仁波切在1983年首次對外公佈這本小冊子, 1995年由塔仁(Taring)夫人在印度出版。
儘管然紮仁波切能夠熟練地使用古典博文,但是他認為在新聞媒體和小學教育中應該使用更為通俗的書寫語言。他對流亡政府編制的教科書的品質感到不太滿意。在一次採訪中,他解釋了自己的觀點:
“我曾經多次勸說達蘭薩拉的圖伯特政府,編寫簡單的兒童讀物或是發行一份使用口頭語言而不是學術語言寫作的報紙,從而讓普通圖伯特民眾有東西閱讀。很多博巴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相信我們必須進行改變。文學語言無助于對普通民眾的教育。這使得普通民眾懵懂無知。在達蘭薩拉,給孩子們教授的語言主要是文學語言,而孩子們無法將這些語言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因為文學語言和普通口頭語言有著不同的語彙、詞形變化和結構。
“我用口頭語言為這裡圖伯特社區的孩子們,編寫了幾本兒童讀物,我還打算將圖伯特文學作品轉變為通俗語言。圖伯特的教育依然過於精英化。”
 |
| 然紮仁波切在裴斯塔洛齊給圖伯特兒童講課 |
若干年裡,在教育眾多的兒童成為優秀的佛教徒和圖伯特人的同時,然紮仁波切也一直堅持自己的寫作,並持續不斷地推出一系列著作和小冊子,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由達蘭薩拉的圖伯特文獻檔案圖書館(LTWA)出版發行。他對他的導師根敦群培翻譯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進行了增補,原來譯著的結尾部分不幸遺失。他還將黎吉生所稱的根敦群培“未完著作”《白史——圖伯特政治史》(White Annals,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續寫至帝國時期的結束。
他還進行繪畫和素描創作:包括傳統的唐卡、油畫甚至還有逗孩子們高興的小卡通。然紮仁波切的藝術作品不僅反映了他的詩歌老師根敦群培的一些自然主義風格,同時還可以看出印度現代藝術傳統的影響,這大概是得益於他在聖蒂尼克坦度過的時光,以及那裡著名的Kala Bhavan藝術學院,這所學院的院長Nandalal Bose的藝術風格深受阿旃陀(Ajanta)佛教壁畫的影響。然紮仁波切還為孩子們的演出寫作劇本並且親自設計服裝和佈景。他教會孩子們,甚至包括女孩子跳寺院的金剛法舞,並讓他們在兒童村的活動中進行表演。
 |
| 然紮仁波切帶領孩子們演唱圖伯特歌曲。 |
然紮仁波切的生活豐富而充實。由於他不是瑞士公民,因此沒有義務參加國民服務,但是他自願加入了特羅根消防隊(Trogen Fire Brigade)。他在那裡的工作,以及後來和其他消防員們把酒言歡給他留下了美好回憶,這些消防員大多是瑞士的農夫和牧民。
他喜歡每晚來上幾瓶“舒晨嘉登”( Shutzengarten)啤酒,偶爾會喝上一杯當地的紅葡萄酒(Dol)。他的煙斗幾乎從不離手。他是一位好丈夫,也是一位盡職的父親,不僅僅是對他自己的子女而言,對他所撫養的眾多的圖伯特孩子而言同樣如此。他們都叫他“爸啦”( Pala),他們或許還依然記得他講過的那些鬼怪故事:比如《昌都的豬頭魔女》(羌都帕覺瑪chamdo phagjoma),《察雅的妖怪》(紮雅冬則drayak dongdre),當然肯定還有《哲蚌寺的驢頭格西》(哲蚌格西崩古drepung geshe bhungu)。
 |
| 然紮仁波切和孩子們一起製作洛薩卡賽(Losar khapsay,即新年糕點)。 |
然紮仁波切還做得一手好菜,是製作肉餡餅(夏帕勒shabhalep)的專家,尤其是那種鬆軟可口的蒙古式肉餡餅。仁波切製作的披薩餅讓人驚歎,可以輕鬆滿足一大家子人的胃口——經常是一家老小還有很多朋友。
 |
| 幾代裴斯塔洛齊圖伯特兒童重聚一堂。 |
儘管然紮仁波切一直以一種非常專注和全心全意的態度進行自己的修行,但他是少數幾位沒有進行過公開傳法活動的高僧大德之一,尤其是沒有以那種正規的寺院方式。他給孩子們傳授佛法並且允許就宗教問題進行討論和質疑。他對我非常耐心,總是盡心盡力地回答我在這方面很多並且經常是幼稚的問題。那種中規中矩的演講方式似乎不合仁波切的風格,他是一位閒適而風趣的人。每次阿尼瑪卿研究會安排他在達蘭薩拉進行一些公開演講,他總是會跑題並且以講一個與主題無關的笑話或故事而結尾。
和另外一位我熟悉的轉世喇嘛塔澤仁波切(達賴喇嘛的長兄)一樣,然紮仁波切也是一位你和他在一起時無需拘泥禮節的人。儘管這兩位喇嘛都是按照宗教學術傳統接受的教育和培養,但是儘管如此,他們兩位的理念和態度都相當令人耳目一新地現代、理性和人道主義。事實上,這兩位喇嘛都有很好的判斷力甚至是很好的個人體驗,從而對根本性的朱古制度(即轉世制度)產生嚴肅的質疑,而正是這種制度最初造就了他們。保羅•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教授在他的一本關於第六世達賴喇嘛的書中,提到“然紮朱古坦率地承認,他不喜歡朱古制度。他講到一個例子,在印度的圖伯特流亡社會找到了據說是一位上師的轉世,結果卻發現這位上師還活在圖伯特境內。”
然紮仁波切一直堅持寫作,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他努力完成了中國前往印度的最早的旅行者法顯遊歷印度(399-414)的筆記,這位元僧人去印度尋求律藏經典(vinaya-pitaka)。仁波切的女兒澤旺曲雅(Tsewang Chogyal)協助他完成了這項工作。在由圖伯特文獻檔案中心出版的這部譯著中,然紮仁波切加上了印度早期的佛教遺跡,彌補了法顯原作的遺漏。他還完成了哲彤家族史的第一稿。2011年夏天,我在瑞士花費了四天時間幫助他核對事實。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
| 然紮仁波切與家人。攝於1988年。 |
然紮仁波切於2012年7月10日離世,享年87歲。他身後留下的家人有妻子桑丹卓瑪(Samten Dolma);女兒茨仁曲珍(Tsering Choezom)、丹增曲珍(Tenzin Choezom)和甘登曲珍(Ganden Choezom);兒子丹增旺波(Tenzin Wangpo)、仁增旺波(Rinzin Wangpo)和很多孫子孫女。
今年的6月30日,仁波切的家人齊集日貢(Rikon)寺,為然紮仁波切舉行隆覺(longchö)儀式,紀念他逝世一周年。
7月10日,曾經出版過然紮仁波切四部著作的圖伯特文獻檔案圖書館和阿尼瑪卿研究會會長紮西次仁啦,在圖書館所在地達蘭薩拉的崗欽吉松(Gangchen Kyishong),為然紮仁波切的文學和藝術作品舉辦了公開展覽。
(我必須要感謝茨仁啦、甘丹啦、旺波啦和TC啦,感謝他們提供的資料和照片;還要感謝紮西次仁啦對我的文章進行一絲不苟的核對,並在我沒有把握的地方提供了更加準確的日期和人名。)
 |
| 然紮仁波切的畫室。攝影:Manuel Bauer |
有關然紮仁波切悼念文章的一些更新
發表于2013年7月18日
不少讀者在評論中索取有關然紮仁波切作品和詩歌的資料。他的一些著作可以在圖伯特文獻檔案圖書館找到,但是他的很多短篇作品和詩歌因絕版而無法獲得。他的遺屬已計畫出版他的文集,並將向感興趣的讀者告知有關資訊。
圖伯特文獻檔案圖書館和阿尼瑪卿研究會會長紮西次仁啦,舉辦了一個有關然紮仁波切的研討會。很多著名圖伯特學者和作家,包括吞紮·阿嘎桑傑Naga Sangay Tendar 啦、紮西次仁啦、阿嘉亞·嘎瑪門朗啦Acharya Karma Monlam la、索朗嘉稱啦(Sonam Gyaltsen la)和瓊茨仁啦(Chung Tsering la),在會上發言。據說,儘管時值季風雨時節,會場依然座無虛席。達蘭薩拉的新聞媒體也參加了會議。
我一定要感謝拉崗曲紮啦( Lhagang Chodak)將我的這篇悼念文章譯成博語並發表在“哈達網”( Khabda)。哈達網的編輯們還發表了多吉旺秋啦(Dorje Wangchuk la )、格西•索朗益西啦(Geshe Sonam Yeshey la)和其他一些人有關然紮仁波切的紀念文章。紮西次仁啦已經寫作了一篇詳細記錄仁波切生平和著作的長文,將會刊登在下一期圖伯特文獻檔案圖書館發行的博語雜誌《当木措》(Tam Tsog)上。
仁波切最後發表的文章是2012年5月13日為流亡報紙《圖伯特時報》( Tibet Times)撰寫的一篇評論,當時離他去世不到兩個月。他在文章中反駁了那些反對圖伯特獨立的言論。這篇文章的英文譯文發表在讓贊聯盟網站(Rangzen.net)。然紮仁波切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藝術型人士,某種程度上不太關心政治。但是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圖伯特境內年輕人的英雄主義行為讓他深為感動,他努力在思想意識領域捍衛他祖國的自由,反駁那些正在對其進行破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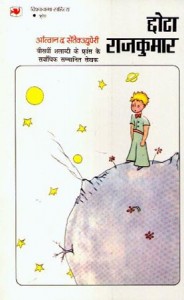 瓊茨仁啦告訴我,他已經編輯了然紮仁波切翻譯的《五卷書》(Panchatantra),這是一部不朽的古印度寓言和動物故事彙編,《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以及其他著名的類似故事集都可以從這部書中找到淵源。此譯著由CTA教育部於2010年出版,並且可以下載免費的PDF版本。
瓊茨仁啦告訴我,他已經編輯了然紮仁波切翻譯的《五卷書》(Panchatantra),這是一部不朽的古印度寓言和動物故事彙編,《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以及其他著名的類似故事集都可以從這部書中找到淵源。此譯著由CTA教育部於2010年出版,並且可以下載免費的PDF版本。
仁波切的一位女兒在電子郵件中對我說,當他最後不得不住進醫院時,他還打算將安東萬(Antoine de Saint-Exupérynovella)的《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翻譯為博語。“他在醫院病床上的最後時日,都在讀這本書的英文版和印地語版,並且做了筆記。他和平常一樣忙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谢谢嘉央诺布先生的文章,让我有机会知晓并且尊敬一位藏人学者。对人与文的热爱不为民族和地域界限。扎西德勒!
回覆刪除藏人的教育是心灵教育。从古代到现代不受理工科教育。在中国藏文的理工科教程为零。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也为零。也就是说教育只局限于文学,而没有一个人去认识用藏语去认识理工科的藏语教程。要认识现代的数理化在中国那就必须学会汉语,在印度自然要必须学会英语。藏人自己没有完整的理工科教育体系。这就导致了人在近代而思维体系在古代的现代的活的博物馆而被人研究。藏人在世界经济和工业领域的零状态的持续时让人窒息的。僧人学佛,俗人信佛。并把它作为藏人文化的根基而社会现实中的进步与落后并无人问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藏人历史的悲剧。尽管尊者方才认识到原来世界不是方的是一个圆的世界时。还有很多人不大服气。对于传统的认识没有改变,没有批判的一概接收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今天,西藏的矿藏被开采,水力资源被毁坏。我们还在口若悬河的念着祈文,被别人抢劫一空的沼泽边洋洋得意的拌着糌粑,心里想着国家主席也许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盘桌腿,拌着糌粑伙同“辣子尕勺”在美餐?对处世的意识和概念相差实在是太远了。别人制造出加油汽车,加电汽车,HO2汽车的时候,藏人才因为会开车而洋洋得意。我们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我们给西藏应该做些什么?难道世代收受布施,和继续保持难民的身份就是藏人的命运吗?
回覆刪除